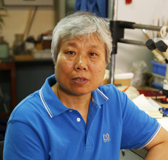
- 未标题-3.jpg.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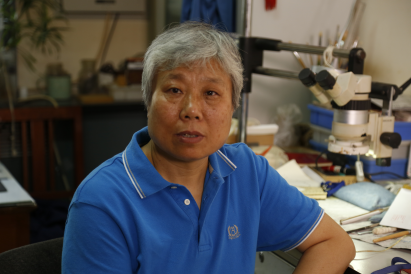
张丽芬
张丽芬,女,汉族,1954年7月出生,河北顺平人。原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级实验师。
1971年9月参加工作,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学习培训。1972年起,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管理处从事讲解工作。1974年起,在河南确山“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5年起,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管理处从事讲解工作。1978年10月起,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馆模型室从事古生物化石模型制作工作。1986年12月起,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助理实验师,其间:1990年3月—1991年2月,赴加拿大阿尔伯特梯雷尔博物馆参加中加合作项目。1992年11月起,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实验师。2001年3月起,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级实验师。2009年3月退休。退休后仍从事化石修理和古生物化石的模型复制等工作。
张丽芬:我在这里度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我从校门走入社会
我们在周口店中学读书的时候,周口店龙骨山准备展览,需要一些讲解员。告诉我们的时候很突然,叫我们几个人过去,读一读讲解词,然后就把我们招到山上去了。我们是1971年9月份来所的,当时从学校招了10个人。10个人中有6个女生,4个男生。去的时候所里特别重视,我们一进所觉得很热闹,还开欢迎会,在欢迎会上还有所里领导和科研人员讲话。对我们这些刚刚来的青年人寄予很大希望,把我们比作刚刚下水的船,今后要我们经得起风浪的考验。当时因为我在学校是班长,所以过来的时候也就负责我们这几个人,相当于小班长。然后我代表这些人讲了话,主要就是针对所领导和科研人员的讲话表个态吧,要向这些老师们学习,以后要尽量地做好工作。反正当时讲的什么内容我也不记得了。因为我们是刚刚从校门走入社会,什么也都不知道,等于是一张白纸。
之后我们就在所里集训了三个月。集训的三个月中,因为周口店要搞整改会讨论一些小样,主要是和人类室的这些老先生们在一块儿讨论,我们也参加。当时感觉很多词都没听过,更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也给我们上一些业务课。上课会讨论小样,下课我们也挖防空洞。另外还参加一些植树活动。所里还给我们组织一些学习,像在山上搞讲解期间,利用休息的时间,把我们带出来去参观其他的博物馆。比如说带我们去自然博物馆,然后去周边那些可以去的地方看一看,增加一些感性认识,然后回到讲解的工作岗位上,更有利于讲解工作。
我记得因为讲解员的学习问题,我曾经也给所里写过报告,强调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因为要给观众讲解,自己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量,所以除了感性的认识,还要增加实质性的业务方面的知识。我希望所里能够派一些研究人员给我们讲课,侧重于周口店的发掘历史,还有一些动物化石的年代等问题,还有地质方面的知识。后来所里基本上同意我们这个报告,然后就在不同时间段,派科研人员下来给我们讲课。
我们当时也跟着去进行过一些地质实习。当时北大的吕遵谔教授常带着学生到周口店实习,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去,看一些化石地点,参加一些地质实习和地质旅行。我记得好像在昌平的一个水泥厂还实习过。还有比如跟周口店有关的,什么14地点了,冰川擦痕了,第四纪留下来的那些遗迹,我们都去过。后来所里派来业务人员组织我们学习,就是黄慰文老师组织这些讲解员的学习。除了业务知识,有时所里的研究人员还临阵磨枪,交我们一些英语单词,比如山上那些动物的名词。总之,所里对我们的很重视,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
几位老先生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我们那时对吴新智先生的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他讲课的次数多一些。还有就是邱占祥先生,他讲哺乳动物进化,齐陶教我们一些有关哺乳动物的英语单词。还有尤玉柱讲地质,还带着我们去搞地质旅行。当时吴汝康也参加讨论一些小样。裴文中和贾兰坡等几位研究古人类方面的老前辈,对我们都挺关心的。裴老有时候去周口店,他总是叼着个烟卷听别人说,说的对的地方他就不言语,说得不对的地方他就哼一声,哼完了以后就给纠正一下。贾老比较亲切,也比较慈祥。裴老和杨老他们,都是喝过洋墨水的,但贾老就不是,所以叫他“土专家”,但是他这“土专家”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那会儿跟贾老一起住筒子楼,没事就跟贾老一块交流,后来也有工作上的联系。我给贾老做过好多东西,做过石器和细石器,他最初到香港大学去讲学,我给他做过宁夏的,还有水洞沟的细石器,他拿过去给人家讲学用。我们刚去所里的时候,杨老是所长。杨老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特别喜欢小孩,我们在他们眼里是孙辈的,所以他特别喜欢我们,爱跟我们开开玩笑,跟我们说说话。他有一次在接待室看到我们,就跟我们讲,你们这些娃娃,以后要好好学习,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失去寸金有可寻,失去光阴无可寻。我就对他说的这四句话印象特别深。杨老希望我们要抓紧时间学习,好好讲解。有时杨老也跟我们开玩笑,还打赌,赌输了还给我们买糖吃。杨老这人特别好,因为他也是九三学社的前辈,我们每年都去给他扫扫墓。不光是杨老,在山上安葬的还有裴老、周明镇周先生、吴汝康,另外还有尹赞勋和贾老。我们九三学社第六支社每年清明前都去给这六位老前辈扫墓,差不多有十年了。
真正投身周口店工作的那些日子
培训三个月之后,我们就回到周口店,跟大家在一起投入了整改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包括做布景箱、搜字、弄铺板等等琐碎的事情。我们10个人,根据个人的情况分到各个小组里面去。当时我被分配做布景箱,就是做树叶、小房子,还有树。做布景箱这个活儿比较脏,有的女生不乐意做,因为和石膏烧手。我当时是负责人,其他人不愿意去,就只有我上了,我就跟着师傅一起,给他和和石膏,做做助手。原来最早的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布景箱,所有的石膏基本上都是我帮着师傅来和的,然后师傅来做。所以从那之后我就跟这个行业有了一点点渊源。后来师傅从所里带一些小的石器标本来山上教我做一做。那会儿我也比较喜欢这个,就跟他学。当时没有别的想法,就觉得博物馆需要多方面的人才,既要有讲解的,也需要有一些技术上的保证,比如说标本坏了,模型坏了,就得修复。所以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学一学,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可以上去把它修补过来。
整改工作做完大概是在5月份,1972年的5月份开始试展。试展之前吴新智写的讲解词给我们。我们10个人5个房间,正好分五个部分,我和蔡炳溪两个分的第一部分。5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真正上岗讲解。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轮着,一个人一个小时。后来我偶尔去看看现在的讲解员,无论是个人的文化素质,还是设备,都非常好,我挺羡慕现在职业化的讲解的。
刚开始那会儿也不知道自己讲解的内容是什么,只是背台词,背下来之后给观众讲。10月份试展结束,正式开展。当时参观的人就挺多的,应接不暇,一天当中讲得口干舌燥,有的时候要讲十几遍。在那段时间接待了不少的观众,好像学生比较多,有部队的,还有厂矿的,还有一些零散的观众,全都是慕名而来。经常是这拨观众转入下一个展室,再进来一拨,就这么轮着走。那会儿我们也觉得特别辛苦,后来所里的领导,包括山上领导,对我们也挺关心的,给大家买点菊花、胖大海,大家就不停地在喝水。
那会儿也比较简单,大家都没有经验,办展览都是全所总动员,所里如果人手不够的话,就从周围的其他省市调一些技术人员过来。比如说当时的那个木工,还有是裱图版和展柜的那些,就是把山西大同的老师傅请过来。还有陕西考古所左崇新师傅,他是专门捏泥塑的。还有从杭州请来的专门搞雕塑动物的老师,当时我们一起来的赵忠义就跟他们去学着捏动物了,后来他也改行了,去搞复原雕塑模型了。当时筹展情形就是这样了。不像现在从设计到影像,都是全套的。真是羡慕现在的方式,我们那会儿太简陋了,还得要节约,也没有那么多钱去花在这上头。
正式开展后,我们也就能接待一些外宾了。那年我觉得接待的观众可以说是数以万计,外宾也得有千人左右。当时这些外宾好像有来自外交部的,礼宾司的,还有轻工部等负责的……都是上面来开了介绍信,然后打电话到所里,尽量安排好去接待他们。刚开始接待的时候我们都有点紧张,后来慢慢就不那么紧张了。
当时在周口店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比较艰苦,由于离家近,一开始我们基本吃住都回家。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要求我们都要搬到山上去住,因为晚上有时候也要组织一些学习。一开始我们住在食堂旁边的一个房间。后来我们就住在老三馆,就是以前拆掉的那个馆。男生住在下面,我们女生就住上面去了,上面相对比较安全。吃饭的问题基本是在山上,但有时也回家去。
心中永远放不下的,还是周口店
工作期间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有个关于安全的事特别有意思。当时所里比较重视的,一个是安全保卫,一个是卫生,还有就是保证馆里面的讲解。李荫芝当时是山上的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在他的脑海里始终就是这三件事,所以他总是给我们灌输这个。有一年夏天,宿舍里比较热,有两个女生就跑到山顶洞上面乘凉去了。结果乘凉的时候,她们发现山神庙底下灯亮着,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李荫芝在办公室跟人聊天。这两个女生就想试试他们的警惕性,于是从山顶洞上面滚下两块石头,正好滚到山神庙的墙那儿。这老李特别警惕,一听见有声音赶紧出来看看,看一看没有啥动静。这两个女生又扔下来两块石头,她们还在上面乘凉,悠哉悠哉的。下面的人可就紧张起来了,马上给派出所打电话,又给部队打电话。部队可能派了一个班还是一个排来巡山,结果那天弄得特别紧张,说有人来搞破坏了。刚巧那天我回家,第二天早晨,老李一看到我就给我讲这个事情,把这个过程跟我说了一下。后来我就上去了,把老李讲的事说给他们听。结果我一说,这俩女生拍着巴掌哈哈大笑说,把他们给吓着了。后来我说你们俩可犯了大错误了,赶快去找老李承认错误去吧。她俩一开始不敢去,后来还是去了,把老李气坏了,让她俩写检查。
我们当初的10个人通过在这里学习,现在发展得都不错。每个人都想着深造学习,提高自己。当然我们10个人当中有学习好的,像高克勤现在在加拿大。1974年的时候,高克勤就是第一批被选上去长春地质学院上大学的。他回来之后又回所,又到地质所,然后又考研究生、博士生,最后出国了。后来他回来之后作为访问学者,在北大任教。我们比较羡慕他,当时学习的时候也挺支持他的。1978年的时候我就离开山上改行了,到所里的标本馆模型室做模型工作。这与我之前做布景箱的经历有一定关系。我现在做的模型跟展览的模型不太一样,我做的模型都是给研究人员作为标本对比用,还有的是用来对外交换用。现在是交换得比较多,因为标本只有一件,尤其是地方上去挖出一件比较珍贵的标本我们只有研究权,没有标本的保管权,所以要做一件模型留下来。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就得要特别的注意,给研究人员用的标本一点儿都不能马虎,必须沉下来学习技术。
丢失的那些头盖骨都有模型,这些模型最早是胡承志老先生做的。胡老先生给予我们的指导确实不错。我曾经接待过步达生的女儿步美林。我印象当中她人很不错,个子高高的。她大概是1977年6月份来周口店。她参观时也提了一些问题,主要就是有关北京猿人头盖骨遗失的问题。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她也特别关心。步达生1921年到中国来的,1929年到周口店。她讲她的父亲1934年在北京去世了。
我们上次去,发现接待外宾的老接待室,现在改成监控室了。那是50年代盖的老房子,我们以前接待外宾都在那里接待。鱼化石因为发现的很多,就没有做过模型。原来我们馆里边的第一部分靠一进门的右手边就是大鱼壁化石,那是真的化石。来参观的人除了关心头盖骨的去处,就是关心化石是不是真的了。周口店的大部分都是真化石,就是即便有一部分补配上去的,基本上也都是正形。正形就是标本,副形就是模型。
20世纪70年代在周口店开始工作的时候,环境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就说周口店前面那条河吧,以前就叫周口河。一到夏天下雨,河面就变宽了。冬天时水也挺清亮的。我记得小时候,水里的鱼特别多,水特别清亮。我们有时候到河边去洗洗衣服,去玩一玩。后来东方红炼油厂搬过来之后,河水就污染了,鱼也就没有了。
当时周口店大概有二十多人在里面工作。早期有老的陈列馆,就是在现在新馆的前面,后来拆掉了。当时主要是以研究为主,没有对外开放。后来大家都想了解,要搞一些科普和宣传才改成了展览馆。
我现在做的小哺乳动物化石的模型比较多。我跟谢师傅俩人是属于高等室老第三纪的,做老第三纪的东西比较多。另外,我也做一些人类化石,现在人类化石发现得特别少嘛,最近他们在山西发现的,拿回来让我帮着做一做。一般做这些都不是展览用的,而是用来交换回去的。因为我们研究完了以后,他们也要陈列。陈列以后,他们就把真的标本收起来,真的标本不往外拿。
去年去新的博物馆参观了以后,我感觉原来虽然咱们国家投入那么多办的展览馆,把化石放在展柜里边进行展览,让大家看。但是要和现在比起来的话,以前我们的“老祖宗”北京猿人好像相比之下有点委屈,现在新馆更大了,设备更好了。但是对这个山上老遗址的改造,我个人感觉不舒服,也许是我们对过去有很深的感情,我就觉得地儿太窄了,把原来的那些地都种上东西了,该开阔的地方还是应该让它开阔一点。当然现在人为地修出一条路,沿着路绕周口店走一圈,也还不错。周口店遗址,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环节,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