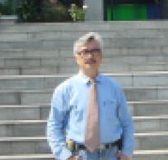
- 未标题-3.jpg.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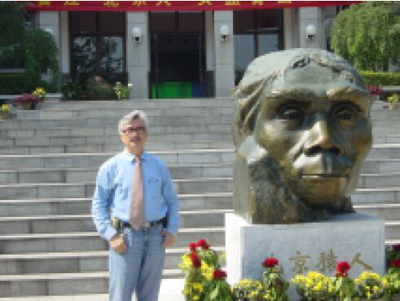
周国兴
周国兴,1937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1957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师从人类学家吴定良教授专修体质人类学。1962年毕业后受聘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事古人类学与史前考古学研究。1979年转北京自然博物馆,从事人类学与博物馆研究至今,其间1985—1992年任该馆副馆长,负责业务领导工作。曾任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博物馆学会、北京市博物馆学会等常务理事及多个学科学会理事之职。
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起源,主张“多源论”,在学术上最早正式提出了“长江流域亦是中华古文明摇篮”的论点。20世纪80年代起,他通过对柳州白莲洞史前遗址的详尽研究,建立了“白莲洞文化系列”的模式,证实了华南中石器时代的真实存在。在人类起源理论研究上提出“劳动”是人类特有的“适应手段”,有初、高两级形态,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初级形式的劳动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但高级形态劳动却为人类所创造,而且在这转变过程中人类祖先的智力和性因素具有强大作用。
在博物馆学的研究与实践中,经他倡议与参与,筹建了9座博物馆,如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元谋人博物馆、南通纺织博物馆和给水技术博物馆等。在推动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发展与复兴南通博物苑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至今已发表出版《元谋人—云南元谋古人类与古文化图文集》《穷究元谋人》《白莲洞文化—中石器文化典型个案的研究》等20部科学专著与科普作品集。
2002年,鉴于在“促进旧石器考古学、古人类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科所做的贡献”,荣获“裴文中科学奖”。2011年,上海人类学学会在复旦大学授予他人类学终身成就奖。1996年被授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周国兴:新研究的基础是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
我在上大学时就开始了与周口店的联系
20世纪50年代因为我看了一本书,对北京猿人发生兴趣了。后来我到我奶妈那里去,在一个坟头看到一个头骨,就把它捡回来了。这本书和这个头骨促使我想学这个东西。1957年我高中毕业时,上海复旦大学第一次招收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全国招生10名,我就报名考上了。1961年我来到周口店实习,在第5地点。在这之前“大跃进”,我们大学里面兴起了一股追赶风,当时我就提出要追赶裴老。1959年裴老到上海去拍《中国猿人》电影,到我们学校来访问,我导师告诉他,我们一个学生要追赶你,他说很好,让我见见,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裴老。第二次是在他的办公室,他说追赶我当然好,但是你要具备很多知识,第一外语要好。然后他还讲到,搞人类学研究就像一个马车有四个轮子,这四个轮子是古人类学、史前考古、地质学、第四纪的地质,还要研究伴生的动物群和植被的情况,你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要具备这四方面的知识。裴老还送了我一些单行本。我当时的论文,是以“北京人”为主的,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跟“北京人”就有密切的关系。
1962年大学毕业了我就去了古脊椎所。我在古脊椎所待了十七年,一开始是裴老带我们到周口店实习。1971年我在周口店值班,王志苗、蔡炳溪他们好几个跟我上课。以后把我调到浙江杭州布置一个以北京猿人作为主体的大型展览,我还把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周轻鼎教授也请到展览组里来。我去了以后碰到一个艺术产生的问题,资料很少。我就给裴老讲了,我说我这资料太少了,您能不能给我提供些?裴老亲自翻译法文的资料,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在牛棚里写的。后来他还给我寄了另一份材料,这些材料太珍贵了。当时的老先生 们对我们这些后辈都是鼎力支持。
我们在元谋发掘的时候发现了非常早的石器。裴老在鉴定元谋人石器的时候,就提了一个石器功能的问题,他说判定一个石器,不是光看它有没有人工痕迹,还要看这些石器有什么用。他说石器无非是三种用处,要么是用尖端刺杀,要么是刃缘切割,还有一个是以重量来打击。
后来我编《北京人》一书的时候,裴老对自己还有一个评价,他不认为头盖骨是他最重要的发现,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个地方(头盖骨)已经在那里了,我是负责它的。工人挖出来人头了,我只是辨认了,其实我最大的功绩是在石器的辨认上,在遭到很多人反对的情况下,我坚持下来了。
1979年我到了自然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是杨老创建的,杨老说古脊椎所是我儿子,自然博物馆是我的女儿,都是兄弟单位。杨老去世了以后,裴老当的馆长,他就对我说去自然博物馆吧,那里没有科班出身的人,你去建立人类室。博物馆是一个能让我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
寻找“北京人”化石
我在编写《北京人》一书时,“北京人”化石的丢失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所以从1979年起,我就关心丢失的问题。首先去协和医院了解化石最后怎么包装的,怎么离开的,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记录,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发信给国外有关学者追寻线索。当时我们收到很多回信,其中有个美国人詹纳斯。尼克松访华以后第一个民间的访华团里就有他。在参观周口店过程当中,他了解到“北京人”化石没有了,就提出来帮忙寻找“北京人”化石。就是这样他寄来了一些照片,后来我写了封信给他。他接到我的信以后很高兴,马上给我寄了记述他寻找“北京人”化石的书,有日文、法文、英文三个版本的。第二年他来找我了,因为牵扯到天津的问题,我请天津自然博物馆也派人来,把胡承志也请来了,还有我们馆的许维枢,我们几个人接待的他。当时我们代表馆里送了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给他,另外我们重新塑造了一个“北京人”的头像,他特别高兴地捧着头像拍了照片。他说他一共获得了三百多条信息,后来集中到了两个人的身上,一个是神秘的夫人,她的丈夫是海军陆战队的。海军陆战队回国以后带回了一箱子化石,这个夫人说她手上有化石,他们后来约定了到帝国大厦86层见面。那个女的去了,把化石照片给他看了。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冲着他们拍照,那个女的紧张地跑了,也没有留地址,后来虽然联系上了,但这个事没有谈下去,不了了之了。
他还提供过另一个线索,他说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一个战士跟他讲,在珍珠港爆发的前夕看到两个人抬了一箱东西在他前面十步远的地方埋下去了。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去了这个地方—前门东大街42号,属于钓鱼台国宾馆的分馆,叫作前门宾馆。管理处的人给了我图纸,也给了我照片。可惜那个地方盖了车库。管理处的人说,只要政府同意我们就可以挖,后来我就向政府报告了。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也没有继续寻找了。
然后我开始在国外举办展览了,展览的时候就传播寻找“北京人”化石的消息。在新加坡搞中国恐龙展时,我们在报纸上登了“北京人”丢失的事情。另外,我们还赠送“北京人”头骨的模型和复原像给新加坡国立博物馆来进行宣传。
1989年我做了一件破天荒的事,过去“北京人”发现纪念活动都是科学院来举办国际会议。1989年那一次,我说裴老已经不在了,我们应该祭奠他,我们自然博物馆应当出面组织一次纪念会。这个纪念会规模不小,有340人参加,影响也很大,很多媒体来替我们报道,我们还给裴老树了铜像,出了纪念邮封。会议后我们出了一本《六十周年纪念会议论文集》,也编了一个《大事记》。《大事记》把历年来发掘的情况做了汇编,每一次挖了多少也做了统计。在保护周口店遗址方面,我提出不要去乱挖,更不要轻易地挖。“北京人”在人类起源研究中有重要的地位,在科学发现史上的作用也非常大。过去对周口店遗址的淘宝式的发掘,大块大块的爆炸,大家都是有些后悔的。所以我觉得周口店未来的工作不是进一步挖掘的问题,而是要好好保护!它的作用应该是充分利用已有材料演示人类演化的过程。另外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应当把原有的材料深入研究,还有已经挖出来还没来得及清理的东西要及时清理,遗弃的大块大块的发掘物要解析它。
我对几位老先生的印象
我跟裴老接触之后,感觉到他很耿直,对下面的人也很亲切。我来到古脊椎所前,我的导师就讲,你去古脊椎所多找裴老。我挺怀念裴老的,他对年轻人很随和,在野外吃东西就跟我们一起坐在地上。他是搞地质出身的,教了我很多东西。在编写《北京人》这本书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做我的后盾。在编书的过程当中,他提出了一个自我评价的问题,他认为头骨的发现固然重要,但是远远不如他识别了“北京人”会制造工具更有意义。当时他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但是他坚持探究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裴老喜欢钓鱼,我陪他钓了好几次鱼。裴老是京城学术界有名的“三条鱼竿”之一。我陪他到洱海钓鱼,钓了半天鱼不上钩。旁边有一个人钓了一条很大的鱼,我就跟他说,我们老先生钓了半天没有钓上,这条鱼你能卖给我们吗?他说,我好不容易钓上的,回去还要煮汤喝。结果裴老挺扫兴的。后来中国自然博物馆协会筹备会在我的老家南通召开。裴老钓鱼瘾又上来了,问这里有没有好地方钓鱼?我说博物馆旁边就是一个大鱼塘。但是奇怪的是,鱼就是不上他的钩!
贾老喜欢喝酒,我还有跟他一起喝酒的照片,我每次去有好酒都给他带过去。他生病吊盐水,我去了以后,我说贾老,你现在喝不了酒了吧?这样吧,跟护士说一说,拿酒往你点滴瓶里加一点。贾老听完就笑起来了。1935年之后,裴老去法国学习,基本上都是贾老主持工作。贾老很勤奋,他是没有上过大学的院士。杨老是陕西的几大才子之一。老一辈学者们的文采都非常好,裴老写过小说,他有一篇小说还入选了鲁迅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当时他也属于“文青”。裴老还喜欢艺术,他写的《旧石器时代之艺术》既风趣又幽默。杨老的古诗词是有名的。从文学修养讲起来,杨老是第一,新文学最好的是裴老。他们过去不仅写人类学、古生物的东西,也写游记、考察记,还有一些诗词文集。
我对围绕周口店进行研究的一些看法
我在古脊椎所,一是围绕“北京人”做了一些研究,然后以“北京人”为基础来研究其他更早的和更晚的人类,基本上都发表了文章。我在古脊椎所工作期间驻周口店时,除了培训,还负责接待,给国外学者和媒体介绍周口店。我曾写了《中国古人类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内容包括周口店的整个发掘过程,然后又再研究了蓝田人、元谋人,这些都牵涉到跟“北京人”的对比。起初,对“北京人”的硏究,是把上下层的原始人都作为一体来研究的。1966年在第三层发现头骨,当时我已经感觉到上下层的个体形态不一样。从距今五六十万年到二十多万年,形态在变异,男女性不一样,年龄大小不一样,进化程度也不一样……实际上我们搞古人类的东西,搞多了就会发现,一块人骨头上会有五六种变异,但往往很多人忽视了这些。
另外,我们要尊重前辈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更是因为他们已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比如说周口店年代测定是综合研究的,十几个单位各种手段都用上,你怎么说他们没有进行研究呢?认为只有自己的研究才是最新的研究,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对前人的工作的不尊重,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不尊重,我是非常反感的。
周口店遗址是个宝,不要随便去开发,不要想去淘宝。当然最近这次发掘,发现用火遗迹是很好的。其实我认为人类的用火是很早的,所以我提出元谋人会用火的问题不是没有根据的,为什么呢?在南非有遗址,已经发现了距今一百六十万年的洞穴里有烧骨灰烬什么的,显然周口店发现用火遗迹应该是意料之中的。
周口店很多东西,我们确实没有很好地考究,看问题难免就比较片面。另外做人类研究,应当综合看问题。首先要精通一门,然后还要扩大知识的领域。现在的研究人员利用了很多新的办法,我觉得有一些手段比我们当时要进步得多,但是总觉得有分量的东西发现得还太少了,关键性的东西发现得太少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们要找的是什么东西呢?应该关键性的东西,如从猿到人转变阶段的东西,比如说从旧石器到新石器转化的东西,这些都是研究演化关键的重点。
周口店要研究得好,应当有一支精干的科研队伍,主要研究周口店本身的东西,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能拘泥于一般的研究。展览水平的高低就是研究人员研究水平的高低。我认为做科研的人要走两个路子,专业的书科普化,让人看得懂;科普的文章专业化,要有知识含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