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学京西土地上的拾荒者

“京西三部曲”系北京知名作家凸凹立足京西之南,向福克纳、诺里斯、怀特、罗曼·罗兰致敬的长篇书系,三部共计百余万字,并于2019年先后推出了《京西之南》《京西文脉》。长篇小说《京西逸民》为北京作协重点扶持原创项目,系“京西三部曲”收官之作,于2020年9月由北京日报出版社推出。
站在前两部创作得失的基础上,凸凹在第三部《京西逸民》中有了更清醒的借鉴和把握,试图写得更独特、更准确,更能呈现真实的京西,折射出变迁中的乡土中国。这也是一部向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的重磅献礼之作。
小说将边缘人——拾荒者绳子引入叙述中心,塑造了中国文学画廊中前所未有的拾荒者形象,真实描摹了农村城市化的艰难历程,深入展现出城市化进程的情感矫正。拾荒者与拆迁办,两次土地腾退背后的矛盾纠葛,乡土与都市的复调咏叹,作者以拆迁为切入点,讲述着京西的大地道德、都市寓言。
近日,由北京作家协会、北京日报出版社主办的长篇小说《京西逸民》研讨会于北京市文联举行,主要从北京文学和边缘人书写的角度,对《京西逸民》进行了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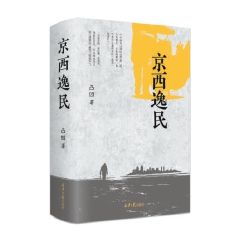
京西
以乡土建立大北京文学地貌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杨庆祥认为,对北京这样一个地域来说,凸凹的写作是非常重要的。怎样写北京,塑造跟它能够对称的文学作品或者艺术形式,也就是“北京文学”,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杨庆祥在“北京文学”这个话题里梳理出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以青年作家如徐则臣、石一枫、文珍为代表,书写外来者在北京的生活,而另外一条线索就是老舍先生开创的,实际上是写祖祖辈辈跟北京都有关系的人,带有乡土性的线索,以叶广芩为代表。叶广芩写的是旗人的子弟,有世家的感觉,而凸凹笔下的故事则发生在京西小山村——史家村。
杨庆祥认为,史家村这样的地域非常有象征性意义,凸凹锚定京西、房山,通过特定空间的叙述,实际上构成了对整个北京叙述,甚至是对当代文学叙述的互补性的空间。在这个互补性的空间里,有很多非常有特点的、可能是不被现代性兼容的人物和事情,比如拾荒者绳子这样的人物,以及他所经历的爱情,凸凹对这个是有自觉意识的,尤其是这种爱情、这种伦理,两者之间的冲突和互补。
杨庆祥关于互补性空间的观点,源自查尔斯·泰勒的理论。泰勒认为,现代性的展开,其实是对多重空间的祛魅。在前现代有多重的互补性的空间,而在这个互补性空间里人可以更整全地安置自己的生命。而如今我们的现代性空间正在变得单一。互补性的空间,比如狂欢节,比如京西的神秘性,这种来自生命的神秘性,才能使得我们得以安置自己的生命。这种神秘,也只有通过小说,通过艺术的方式才能表现出来。
杨庆祥也认为,不仅是京西,京南、京北都可以为北京文学建构新的版图。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写作可以跟外来者的书写,跟徐则臣他们的书写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从而建立真正的大北京的文学地貌。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王德领认为,写北京的作品现在有很多,量很大,但好作品还是少。而且,北京文学中更多书写的是“老北京”,也就是像叶广芩一样,写皇族的北京,强调与过去的连接,更加典雅。而现在写北京怎么写?王德领认为,北京现在已经是一个“让我们日益认不出来”的城市了。从明清古色古香的城市,到新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北京的城市性格变得十分复杂,实际上比上海更难把握。王德领举了上海文学最近的代表作《繁花》为例,这本书被认为是书写了“上海人的上海”,与王安忆为代表的“普通话的上海”很不一样。王德领回忆金宇澄曾对他说:“(《繁花》)选择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因为我这个书是上海的。”在《繁花》中,金宇澄把上海的城市性格,以非常个性化的,非常史诗化的方式勾勒了出来。
那么,对于北京这个城市,怎么把握它?确实比上海有难度。王德领认为,徐则臣、邱华栋书写的是“外来人的北京”,叶广芩是“皇族的北京”,王朔是“大院的北京”,此外还有“胡同北京”。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集中在北京主城区这一块,这一部分北京的城市性格,是从老舍开始的。但北京还有另一块,就是北京周边的乡村——北京范围不停外扩,把周边的区县都划到北京来。“凸凹兄在京西乡土一直在开拓,他把北京乡土性这一点展现出来。上海基本没有乡土性,北京有乡土性一面,凸凹兄把乡土这一块写出来了。其实乡土的北京在最近这些年非常欠缺,除了凸凹之外,我想不起哪个作家孜孜不倦地用大体量的书来写它。”王德领说道。
作为“京西三部曲”之一,《京西逸民》正是以对京西的描绘,填补了北京文学的一块空白。书里出现的如“落枕”、“害口”等表达,都是京西特有的语言,另外还有京西独有的丧葬礼仪等,都是取材于民间的真实素材,代表了京西独有的风貌。
逸民
神秘的日常生活与独一无二的小人物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则认为,相比于“北京”,《京西逸民》更吸引他的,是其中所描绘的日常生活的神秘性。“表面上看,凸凹写小说是为京西立传,也就是巴尔扎克说的‘长篇小说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但是我读到这部小说的时候,反而不是这个看法。”敬文东说,“日常生活,包括像绳子这样的人物的日常生活,我们常常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我们日常生活是神秘的。什么叫神秘性?有无数个可能世界,而且这无数个可能世界中,能够成为现实世界的每个可能世界机会均等,但是,只有一个可能世界会成为现实世界。”换言之,每个人能成为自己,都是“命中注定”,都是“天意”。绳子这个拾荒者的生命形态中的神秘性,包括他与白德臣这样一个领导的故事,都触碰到了日常生活当中的神秘性。敬文东认为,“这才是这部小说吸引我的东西。”
绳子,是《京西逸民》的神秘所在。他虽身为拾荒者,精神却极端自由,能够阅读费尔巴哈、黑格尔,并将其思想付诸实践。为什么要塑造这么一个特殊的边缘人形象?北京作协理事、北京评协副主席解玺璋提出了一个疑问:“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逸民”在古代话语中应是一个特定的称谓,以此来命名绳子这样的人物,是否合适?
如何理解“逸民”这一概念?中国艺术报文艺部主任邱振刚从中国古典审美话语体系出发,追溯了“逸民”的源头。“中国古典审美的话语体系里面,‘逸’常是高段位的概念,提到‘逸’字,肯定是想到古代那些高人隐士,比如像庄子、李白、陶渊明、袁枚。同时这个字还意味着非主流化、非体制化。但是绳子这个人物,跟我们传统概念里面的高人隐士不一样,他没有那种仙风道骨,也没有某种人生成就。”邱振刚认为,像李白、袁枚、陶渊明、唐伯虎这样的人物,在诗词、书画方面有着非常高的成就,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这种成就支撑他的人格或者支撑着“逸”的生活方式。但是,从绳子的生活方式和心理因素来说,他又的确是非主流化、非体制化的——绳子经常引用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话。在《京西文脉》里,引用了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这句话。如果从绳子的思维方式来看,人诗意地栖居,这里的“诗意”不是说生活得多么精致,语言、行为多么优雅,多么高品质,而是他知道自己生而为人,知道自己是独立于天地万物、独一无二的生命,是对自我的确认,对生命意识的张扬。“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人物恰恰是构成三部曲里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这么一个非主流化、非体制化的形象,恰恰跟《京西文脉》里面的知识分子形象、《京西之南》中乡村干部形象,共同组成了凸凹老师的自我的人格、他的灵魂。这三个面相,也就是说他自己的心灵世界、他自己灵魂的三个切面。”
邱振刚表示,绳子这个形象,以前在文学史上几乎没怎么出现过。“他靠捡垃圾为生,他有一个住处之后并不太感恩,他并不把帮助自己获得住处的白德臣太当一回事,他还从道德上毫不掩饰对白德臣的藐视,他作为拾荒者,他喜欢看哲学书、看黑格尔、看费尔巴哈。而且他能学以致用,把从哲学书里面体会的思维方式用来解读现实世界里的很多问题。这么一个形象很难解释,因为以前的人物形象往往是某一个群体或者某一个阶层的代言人,而绳子这个形象,我看不出他背后代表着什么,他只是他自己。”
那么,到底为什么要塑造这么一个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小人物,并以“逸民”命之?凸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就是要探讨我的精神高度、思想深度和人性广度,我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我到底怎么超越我自己。我发现,在写作过程中,我已经跟现实身份脱离了,逃逸了。‘逸民’这个词,我取它的一个含义就是藏在民间的、非主流人群里面的高人和能人,甚至还有怪人。另外还有一种动作上的含义,就是从主流里边逐渐逃离、疏离。”
实际上,绳子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来源于凸凹的生活之中,就出现在他所居住的小区。“这个人依然在我们小区活跃着,每天意气风发地捡废品,身姿挺拔,步履矫健。”凸凹说道。(白杏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