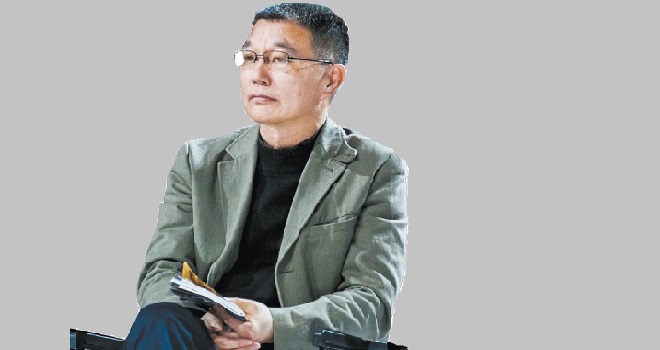
- “伍姆雷特”的北京故事

作家止庵
“伍姆雷特”之名的由來
本文題目之所以叫“伍姆雷特”的北京故事,主要是着眼於止庵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説《受命》裏,冰鋒這個人物形象的設計理念。
止庵是一位學者型作家,曾發誓“讀盡天下書”。棄醫從文之後,致力於張愛玲作品和周作人作品的研究推介,撰寫《周作人傳》;其閱讀領域汪洋恣肆,於古今中外的文學、歷史、藝術經典多所涉獵,並以寫書的方式記錄心得——比如記述讀書歷程的《插花地冊子》,研讀古代經典的《樗下讀莊》,研修歷史學的《神拳考》,基於美術館看畫經歷闡發審美體驗的《畫見》等。僅從涉獵範圍,已經足以令我們一窺其雄心與淹博。至於懷念母親的長篇散文《惜別》,則以平易筆調,敘寫沉痛心境,行文頗得周作人的沖淡神韻。上述種種,一旦被這位學者型作家以醫生的冷靜與縝密、詩人的熱腸與超拔,一統於小説創作,那麼,這種創作所誕生的果實,其滋味很可能是相當獨特的。
《受命》通篇的架構,堪稱一個“伍子胥與哈姆雷特合體”的當代北京故事——主人公是陸冰鋒,一位執着於替父報仇的孤獨英雄。在非常年代,冰鋒的父親由於同事祝國英的告密和此後種種陰差陽錯,從一個不幸落入另一個不幸,最終導致自殺。小説開篇,就是主人公從即將患上阿爾茲海默症的母親口中,聽到了仇人之名,從此開始了曲折的尋仇、報仇之路。這條路,與冰鋒在1980年代作為口腔科醫生的謀生之路、作為文學愛好者(一直構思為伍子胥寫一部詩劇)的求索之路並行交錯。他於此間結識了業餘寫作者平果、葉生,醫院護士蕓蕓等人,從而展開了一連串情、愛、性的瓜葛,而在這一系列的瓜葛之中,冰鋒、葉生、蕓蕓、平果等人的形象,也就越來越豐滿。
冰鋒的形象設計,既有伍子胥式的對於報父仇的執着,又有哈姆雷特式的對於報仇的猶疑——源於其精神追求(善)和生命欲求(美)的矛盾衝突。那種執着,使得主人公具有可敬的英雄氣息;那種猶疑,又使他具有可親的君子魅力。比如,冰鋒的執着源於一種執念:“歷史不能總是一筆糊塗賬,個人也要負責”;而冰鋒的猶疑,則表現在例如明知仇人之女葉生暗戀自己,卻一再壓抑衝動,提醒自己“不能佔她的便宜”,否則,復仇這件事就會變得“不乾淨”了。其實,無論是執着還是猶疑,都體現了冰鋒那種於今已經罕見的“義士”特徵——對於“義”的追尋。
我們知道,“義”這個字的繁體寫作“義”,從羊從我,是個會意字,《説文解字·我部》解釋為“己之威義也”,也就是“儀”(今天的“儀”字);後來所説“仁義”的意思,本字是“宜”或者“誼”,表示合於宜,合於情誼(情之所宜)。威義(或説威儀)之“義”,從羊,羊表善美之意,可知美、善、義,都從羊,意思也相類。所以,一個“義”字,包含兩個詞,一個是後來的威儀的“儀”,一個是合宜的“義”。
“義”字包含的兩個意思“合宜”和“威儀”,幾乎可以説是冰鋒這個人物形象設計的濃縮詮釋——他對父親之死抱有的不平之氣,體現了對於“合宜”的追求,所謂的報仇,也就是為了伸張這個“合宜”;在那個冰鋒自以為一切安排就緒的晚上,他帶着準備好的一應工具前往祝家,無論成敗與否,我以為都是完成了那種“威儀”,是對死去的父母實現了一種承諾,也是對“平民的尊嚴”的一種強調。而“義”字從羊,羊表善美,與“利”絲毫無關,尤其是在古代,“義”和“利”,是截然對立的概念,這一點,也在冰鋒形象上體現得相當鮮明。故事發生的1984至1986年,正值改革開放之初,人心波動,票證供應行將結束,市場經濟緩緩開啟,平民百姓經過多年的精神和物質匱乏,開始排隊購買冰箱、電視,開始追求物質享受,消費主義漸漸抬頭,而冰鋒則是逆潮流而動,不停地回望過去,思索過去,一心惦記為父輩的恩仇做一個了結,此間,無論葉生的戀情多麼純潔熱烈,蕓蕓的做伴多麼溫暖體貼,甚至蕓蕓和弟弟鐵鋒以同去深圳為邀約,葉生以同去美國為表白,都不能最終動搖冰鋒的決心。
然而,冰鋒的決心越是堅定不移,或許越是註定了他的悲劇命運——與哈姆雷特不同、與伍子胥相似,他的悲劇性的一個特點,是要與時間賽跑 —— 祝 國英一齣場,就是個垂垂老矣、茍延殘喘的病人,這也就註定了,冰鋒必須分秒必爭。冰鋒形象悲劇性的另一個特點,也就是使他成為無可替代的“這一個”的特質,是他與時間賽跑的同時,也與空間的劇烈變動相牴牾——這一點,在那個夜晚,冰鋒於衝動之中帶着葉生去和平裏,想要在父親辭世的破敗地下室向她傾訴一切原委的時候,卻見到了那所樓房被夷為平地之後留下的深廣黑洞。這象徵了記憶的缺失,以物理空間的變幻揭示了記憶的脆弱,進而凸顯了冰鋒要與之抗爭的那個龐然大物,有如天文概念中的黑洞一樣,既難以戰勝,又難以逾越。
如果説這個人物形象的設計,最初是源於某種概念或理念,運用了經典的骨架和隱約的背景,那麼,由於作者調動了自己的青春記憶和大量的研習功課,填入了日常生活的豐盈血肉,就使之變得親切、結實、飽滿;同時,又借助與兩位女主人公的互動,使人物塑造變得可信可感。
飄搖的離弦之箭
有過一定寫作經驗的讀者都知道,一部作品的好壞,往往在題目落實的瞬間,就已經註定了大半,比如《尤利西斯》,比如《狂人日記》。《受命》題目一齣,這個雙聲詞的兩個去聲,似叩門,似心跳,似重拳,以其沉重低回的音韻,給整個故事預先籠罩了某種悲劇氛圍,讓主人公背負了沉重的使命,讓故事從第一章得知仇家名字的一刻,就開啟了敘述的離弦之箭。
然而,這支離弦箭,在《受命》故事中,其路徑註定是飄搖的——因為兩位女主葉生和蕓蕓的出現,從兩人各自的方向發出引力,使得冰鋒的復仇,多次偏離了既定的方向,與此同時,卻也使得故事的推進峰迴路轉,並借由種種回轉,展現了1980年代北京獨特的人文與地理景觀,揭示了時代變換中的世道人情,使得小説容量更趨厚重。
葉生的形象設計裏面,可能埋藏着邏輯上的雙重悖論——由於身為祝國英的女兒,所以她是冰鋒所知唯一的可以近距離接觸仇人的途徑,而與此同時,與葉生之間的日久生情,又導致了冰鋒對報仇一事的遲疑徘徊;而葉生性格的極其單純和強烈征服欲,又讓冰鋒於兩性關係中表現出的遲疑,在她眼中平添了致命的自尊與自持的魅力。基於這樣的雙重悖論,葉生越是可愛,冰鋒對復仇也就越是遲疑;而他的遲疑,又進一步增加了他的魅力。寫到這裡,想起一個細節,就是小説裏不止一次通過冰鋒的視角,描寫葉生幾乎是站立在腳蹬上躍動的騎車姿勢,似乎暗示了兩人關係所可能展露的那種野性與狂飆。
如果説,葉生是白富美式的女神般的文藝青年,那麼蕓蕓的形象則幾乎處處與之相反,滿了市井煙火氣與務實精神;如果説,葉生對冰鋒是崇拜和順從,那麼,蕓蕓則是想要一味地控制和利用。不過,假若跳出故事情節來看這個人物的設計初衷,我覺得蕓蕓形象或許有這樣幾種作用:其一,她在冰鋒的徘徊期出現,使得“報仇”這個離弦之箭幾乎隱而不顯(實則隱匿於暗處),使得敘述的主線一下子蕩了開去,讓小説出現轉折,同時也寫出了醫院的改革層面和由此引出的蕓蕓、鐵鋒等人辭職去深圳發展,從而呈現了1980年代下海大潮的冰山一角;其二,冰鋒與葉生頻繁往來,思想交流到了相當的深度,葉生又是那樣可愛、主動,兩人之間卻幾乎沒有身體接觸,這一點,可能會使身心成熟的讀者對冰鋒産生某種誤解,那麼蕓蕓的出現,兩人之間正常的雲雨生活,使得這樣的誤解得以冰釋,從而也就對冰鋒此前此後在與葉生共處時的自我壓抑,印象更加深刻;其三,蕓蕓是蕓蕓眾生裏的弄潮兒,是一種成功型人格,他們天生就有着敏銳的嗅覺,知道自己怎樣做才能得到成功,他們是“喻於利”的,是與冰鋒恰好相反的人格類型,從反面烘托了主人公義無反顧的選擇。
蕓蕓走後,葉生再次出現在冰鋒的生活中,兩人以更快的速度相互靠近,甜蜜而又危險——這時候,産生了一個巨大的懸念,那就是冰鋒這個仇,究竟報了沒有?冰鋒和葉生,最後是否走到了一起?雖説是開弓沒有回頭箭,然而到了第四部的結尾,敘述在冰鋒的角度戛然而止,於是那個一直飄飛在空中的箭鏃,它就懸置在那個時間節點,好像是從文學的角度,應和了哲學家芝諾“飛矢不動”的那個命題。
眼睛與腦筋的體操
我們説,閱讀好的小説,是腦筋的體操;而閱讀學者型作家的小説,則同時也可能是眼睛的體操,因為你看到的每一個充滿畫面感的細節,都可能經過了反覆的考證掂量(比如1980年代飯館點餐的價格表,比如葉生和蕓蕓的衣着),都可能經過了精心的篩選、提煉(比如與仇人之女一起看的電影《罪行始末》,一定是當年北京影院公映的影片),或者可能還是審慎的用典——這是我在翻閱止庵《畫見》一書,看到他對巴爾蒂斯畫作《房間》《客廳》的評論時候忽然領悟到的——因為那兩幅畫中女性的姿勢,幾乎與葉生在冰鋒的科室看牙、在冰鋒的平房小屋床上看書的姿勢一模一樣,是一種準備“慷慨獻身”的姿態——充分説明作家是動用了自己幾乎全部的人生儲備,從理性到感性,從形而上到形而下,來創作小説的。
談到作家的人生儲備,或許就不能不提《受命》扉頁上的引言:“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莊子·人間世》”,這裡,十幾個字的引言,可以延伸的關鍵詞至少有三個:受命,飲冰,內熱。“受命”,已選作題目,前文已經詳述;“內熱”,暗示了主人公貫穿於小説中的內心焦灼;“飲冰”,則讓人猜想:究竟誰是他所“飲”的“冰”呢?葉生?蕓蕓?……同時,對於讀過《樗下讀莊》的朋友,或許還會想起止庵在書中不止一次提及的“吾喪我”,這個概念如果再與作者創作的冰鋒這個人物結合起來,其中的層層意思,值得我們回味與探究。
説過引言,或許還需要提一下尾聲。重讀這部小説才發現,手不釋卷的原因,其中之一是作品具有一定的推理小説色彩。這一點在尾聲部分,讀者通過鐵鋒之口,對書中主要人物於那個命運攸關的晚上之後的人生軌跡,有了一種發動眼力與腦力、完成拼圖般的一一落實的感覺,唯有那個“飛矢不動”的時間節點,是一個空白。不過,在尾聲部分,隨着鐵鋒描述三十年後冰鋒的頹唐,萬里之外葉生對於異性的恐懼,我們或多或少可以用想像的畫筆來填充,當然,這對讀者是一種考驗,也是一種挑戰。
説到“考驗”與“挑戰”,對於作家而言,一部小説的創作,又何嘗不是如此?閱讀《受命》之後,我在讀書筆記裏,套用《庖丁解牛》的一句寫道:“止庵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這裡,小説家止庵所面對的“牛”,應該是如何創作一部好看而又深刻的小説的玄機。面對這個玄機,作家是否達到了庖丁解牛的境界?這就是需要廣大讀者來回答的問題了。我的回答,則是一部電影之名:“自己去看”。(韓曉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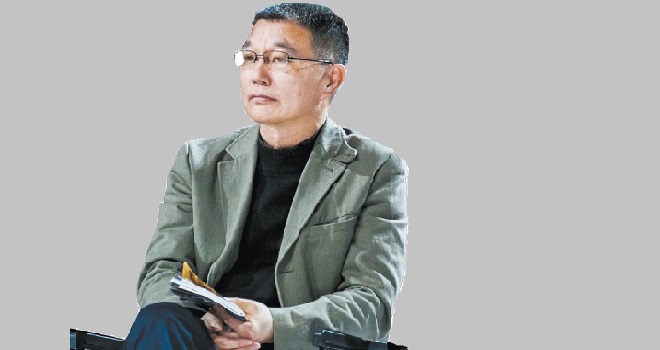 “伍姆雷特”的北京故事
“伍姆雷特”的北京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