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cuile315.jpg.jpg
原標題:秋風秋雨今猶在 秋瑾故居在城南

南半截衚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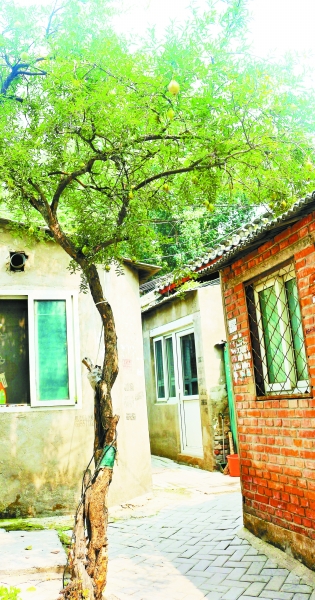
石榴樹

紹興會館石碑
一百年前秋瑾在北京的住所現在誰人知曉?誰能講述她在北京的舊聞?行走在南城衚同裏,尋覓這位偉大的女性革命家當年的蹤跡,我們看到的是樸素的日常,人們祥和地生活在這片天空之下。四合衚同、青磚黛瓦,歷史的時光似乎未留下十分刻薄的痕跡,城市的繁華中依舊點綴着老北京的樣貌。
秋色明凈,如同被纖纖素手反覆擦拭過的天空上挂着一輪又大又亮的玉盤,月光如練,盡數傾瀉在這北京城墻下的連片衚同中。農曆八月十五,正是闔家歡樂,共度中秋之時,卻有一女子,淚灑籬下菊花,遙想離浙八年,如今小住京華,更見中華四面楚歌,列強侵逼,而自己卻為家庭所縛,無途投身救國,口中喃喃念道:“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莽莽紅塵,何處覓知音啊?此女子並不是其他人,正是隨夫赴任的秋瑾。
中華歷史上下五千年,傳奇之人不勝枚舉,但秋瑾這一女子可謂人如其名,瑜瑾美玉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所示,”此謂秋瑾也。她出身於官宦世家,其父秋信候任湘鄉縣督銷總辦時,將她許配給與曾國藩有姻親的湖南雙峰縣王氏,富家子弟王廷鈞。“到了擇親的時光,只憑着兩個不要臉媒人的話,只要男家有錢有勢,不問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壞,學問高低,就不知不覺應了。”(秋瑾《敬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這就是對當時訂婚的真實寫照。兩家經濟地位的不平等,以及舊式婚姻的婆媳關係,加之封建制度中的盲婚啞嫁,使得秋瑾難以與丈夫志趣相投,無法得到足夠的感情慰藉。她雖有謝道韞之才,婚姻卻局限於思怨之中,幸而常與唐群英、葛健豪往來,或飲酒賦詩,或對月撫琴,或下棋談心。三人皆才英出眾,並稱為“瀟湘三傑”。唐群英作為中華民國締造者之一,同盟會的第一個女成員,更是與秋瑾被後人並稱為“辛亥革命的孿生女兒”。
秋瑾先後兩次來京。1900年秋瑾丈夫王廷鈞捐得清廷戶部主事的京官,她也隨之來到京城。首次入京,一説秋瑾居住在南橫街的一個小宅子中,另一説秋瑾暫居於繩匠衚同。繩匠衚同建於明代,1965年改名為菜市口衚同,位於原宣武區中部,北起騾馬市大街,南至南橫西街,因為鄰近菜市口而得名。筆者走出菜市口地鐵站,目光所及之處現代建築鱗次櫛比,哪有一點衚同的樣子。出地鐵站向北走,在北京鶴年堂中醫院門口遇見一位家住法源寺的阿姨,“菜市口衚同早就不見了,之前政府對衚同進行開發了,現在叫菜市口大街。”而菜市口刑場,也隨着清王朝的覆滅而了無印跡了。而我們不曾忘,亦不能忘,那個“去留肝膽兩崑崙”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便是在菜市口以熱血洗污政,以身殉道。譚嗣同家住北半截衚同,如今的譚嗣同故居,也成為了北京衚同中的一景。這位維新派人士不懼生死的精神也頗為秋瑾所推崇,這才有了後來的秋瑾傚法,決心以一死表明獻身革命之志這一説。
1901年,八國聯軍進犯北京城,秋瑾不得不隨丈夫暫回湘潭。與好友唐群英談論此次經歷,唐群英憤慨説道:“國之興亡,匹婦亦應責無旁貸。”由此更堅定了秋瑾的救國之志。1903年,她第二次隨夫赴任,來到北京。此時的北京,雖然四處嚴禁重重,但新的生命和力量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的壓迫下頑強地成長着。這一次,她暫住在南半截衚同。
南半截衚同,大約三百多米長,寬窄適中,現如今能如此保留着原貌的衚同已然不多了。筆者向路人打聽了南半截衚同七號,隨後在一個普通的四合院門口找到了一塊石碑,上書“紹興會館”四字。一進門便是一棵碩果纍纍的石榴樹,依然生機繁茂,但裏面的人們早已説不清魯迅原先住過的老房子的位置,也説不清秋瑾是否在此居住過了。
秋瑾第二次來京,她決心自費東渡留學,投向革命救國和宣揚女權的道路。但這遭到了丈夫王廷鈞的反對。在女兒燦芝的回憶錄中,父親“王廷鈞原是一個年少風流的公子哥兒,到了北京以後,被一班朋友們帶着,成天價在外面酒肉徵逐,後來又結交上了幾個貝子貝勒,常常是花天酒地的混在一起,有時竟徹夜不歸,甚至臥倒在酒甕的旁邊,沉醉不醒,所以夫妻之間,時相勃谿。”兩人爭吵最厲害的一次,便是中秋之爭了。秋瑾後來的朋友徐自華曾在回憶錄中寫到,王廷鈞原説好要在家宴客,囑秋瑾準備。但到傍晚,就被人拉去逛窯子、吃花酒去了。秋瑾收拾了酒菜,也想出去散心,就第一次着男裝偕小廝去戲園看戲,不料被王發現,歸來後動手打了秋瑾。她一怒之下,就離家出走,在泰順客棧住下。於是有了“滿江紅·小住京華”高昂之作。
“苦將儂、強派作娥眉,殊未屑!”在北京的秋瑾,擺脫了公婆的束縛,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禮,越發不屑屈身做一個貴婦人,嚮往着挽救民族危亡,解放婦女平等自由的生活。她結識了當時京師大學堂日本教習服部宇之吉的夫人繁子,學習日語,並結識了書法家吳芝瑛。吳芝瑛曾發起了“上層婦女談話會”和“婦人不纏足會”,兩位才女成為金蘭之契。離家出走後的秋瑾便住在吳家,雖得吳芝瑛出面調解夫妻矛盾,但秋瑾已不願意回到倍感束縛的家庭之中。她閱讀了大量新書報,並從北京趕赴天津,結識了當時《大公報》的女編輯,同是女權運動的首倡者之一,呂碧城。呂碧城也是清末“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她在《大公報》上連番發表鼓吹女性解放的文章,倡導興辦女學,因此與秋瑾相見甚歡,不到四天便結為密友。秋瑾赴日留學前,曾邀這位密友一同赴日,而呂碧城“持世界之人,同情於政體改革”,願意繼續留在國內辦報,以“文字之役”,與秋瑾遙相呼應。
1904年7月,秋瑾東渡日本,此後開啟了她轟轟烈烈的革命生涯,先後結識周樹人(魯迅)、蔡元培、徐錫麟等人,加入光復會、同盟會,一同為辛亥革命“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註定是革命史上濃墨重筆卻又風雨飄零的一年。這一年,先孫中山“黃岡起義”失敗,後徐錫麟在安慶起義失敗,其弟證詞中牽連秋瑾。七月十三日,秋瑾被捕。在燭火昏暗的牢獄中,面對着審訊者的一再逼問,她寫下“秋風秋雨愁煞人”,別無他言。高墻之下,她透過狹窄的窗,似乎已感應到自己的命運同這鐵騎踐踏下頑強萌發的種芽深深地聯繫在一起,決心熱血澆灌,慷慨就義。僅四年後,辛亥槍聲響徹武昌街頭。或許,沒有秋瑾的辛亥革命依舊會成功,但是沒有秋瑾的辛亥革命必將缺少一段美麗的傳奇。“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她在京城的豪俠之氣,依舊伴隨今天的秋風秋雨同在。(顏穎 王冬冬)

 cuile315.jpg.jpg
cuile315.jpg.jpg